目前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,2020年2月11日,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发布会,宣布将其命名为COVID-19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全国人民与广大医护工作者一道,携手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。在这场与疫情的生死较量中,对我们的防控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次严峻考验。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的经验总结,以及临床救治经验的积累、疗效的观察、科研的推进等,新冠肺炎患者中西医结治疗取得了肯定的效果,辨证论治的中医药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,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没有停止过,在一次次的与疫病的抗争中总结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,形成了祖国医学认识和防治疫病的了理论体系。这里笔者将就祖国医学对疫病的认识及防治理论进行梳理与探讨。
祖国医学对疫病的认识
早在殷商甲骨文就有卜问商王是否传染上“疫”和能否医治的卜辞。这说明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对疫病传染已有了朴素认识。
先秦时期的医学经典《黄帝内经》已明确指出“疫”和“疠”是极易传染,病状也多相似的疾病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刺法论》道: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。”《素问·六元正气大论》又说:“其病温疠大行,远近咸苦。”“疠大至,民善暴死。”这又对疫病的传染特性和致命危害加以描述。
东汉中后期,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,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记录有10次疫情,尤其建安年间(196一219),疫情持续时间之长、死亡人数之多,是历史上少见的。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写道:“余宗族素多,向余二百,建安纪年以来,犹未十稔,其死亡者,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”。以至呈现“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”的悲惨状况,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,张仲景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,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,著成《伤寒杂病论》,创立六经辨证体系,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,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、流行病的专著。《伤寒论》对传染病患者的症状和脉象等加以详细论述,对人体感发于“寒”与“风”等致病因子作用下所反映的各种证候加以分析综合,取得了对各种传染病演变规律的认识。该书极大地提高了疫病医学的救护水平,是发热性传染病的医学经典。
晋代医家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》中首次将“疠气”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相互传染的特点,开后代温病学之先河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·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》中认为,“伤寒、时行、温疫,三名同一种……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,名为温病。”并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、老君神明白散、度瘴散、辟温病散等治疗、预防温疫的方剂。书中记载了以药物少许,纳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,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。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带于胸前、挂于门户、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,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,流传很广,沿用至今。
南北朝时期,南朝多流行温热疫,陈延之率先提出了“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”的看法,在《小品方》中阐述了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。
隋代医家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,其中提出的“乖戾之气”是关于传染病因的新探索。该书还对疫病传染的致病因子进行探索,使传染病的病因接近了细菌的发现。
唐代医家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和王焘的《外台秘要》载有多首治瘟、辟瘟方剂,《千金方》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。
金元时期著名医家李东垣在《内外伤辨惑论》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,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。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,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,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,其实就是鼠疫(《中国医学史略》)。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,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。《东垣试效方》还记述了泰和二年(1202年)一次疫病流行,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。
明末医家吴又可(名有性),亲自参与了崇祯辛巳(1641年)之疫的救治,1642年,吴又可“静心穷理”,集“平日所用历验方法”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——《瘟疫论》。《瘟疫论》中说:“一巷百余家,无一家仅免,一门数十口,无一口仅存者”。《瘟疫论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,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其成就有三: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,“杂气”说,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。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,邪自口鼻而入,侵入膜原。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,疏利透达膜原法,创立达原饮治疗,提出“客邪贵乎早逐”观点。他的温病学说在病原体、传染途径、特异性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见解。
到了清代,余师愚在吴又可《温疫论》的基础上著有《疫疹一得》,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,指出“一人得病,传染一家,轻者十生八九,重者十存一二,合境之内,大率如斯。”并根据暑热疫的病征特点,创立“清瘟败毒饮”一方,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。
清代医家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,在所著《疫疹一得》中他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。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,指出“一人得病,传染一家,轻者十生八九,重者十存一二,合境之内,大率如斯。”并根据暑热疫的病征特点,创立“清瘟败毒饮”一方,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。
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《霍乱论》一书,20多年后在上海“适霍乱大行”,于是重订《霍乱论》,名为《随息居重订霍乱论》,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,如连朴饮、黄连定乱汤、燃照汤、蚕矢汤、甘露消毒丹等。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。
清代疫病学派著名医家之一杨栗山,著有《伤寒温疫条辨》一书,认为温病的病机是“邪热内攻,凡见表证,皆里证郁结,浮越于外也。虽有表证,实无表邪”。他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。
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、薛生白的《湿热条辨》、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等诸多温病学著作中的“温热病”、“湿热病”等,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,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,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,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今天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。
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,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。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,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,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。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,还没有定论,但到明清时,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。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,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。
由此可以看出,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,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,他们在继承中医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,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,不断创新,取得了显著的疗效。张仲景解表散寒,李东垣补中益气,吴又可燥湿解毒,余师愚两清气血,王孟英清热除湿,杨栗山升清降浊,这些抗击疫病经验经过凝练,上升为新的理论,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,丰富了中医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。疫病不同,治法不同,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。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,分析疫病的病因、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,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。
祖国医学对疫病病因病机、病位症状的认识
祖国医学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,认为自然界气候、环境的变化对整个生态大系统有直接的影响,在正常情况下,微生物与人类能够和谐相处,生态系统保持有序的平衡状态。当发生自然灾害、战争、人口大量流动以及气候的异常波动时,整个生态系统的外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,导致微生物间的生克规律发生混乱,一些病原微生物发生变异或大量繁殖,失去相对稳定性,最终导致瘟疫爆发流行。
对病因病机的认识
在中医学最早的典籍《黄帝内经》中,就已认识到某些温病具有传染性,并以“疫”名之。《素问?刺法论》日: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。”古代医家在诊治各种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,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,积累了丰富经验,尤其是在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上,更是形成了独特的理论。认为疫病的发生与其特殊的致病因子密切相关,其致病的病机主要是禀赋薄弱,正气亏虚,戾气乘虚借口鼻等道侵袭人体,邪气匿伏于膜原,以致阴阳失调、上干于上焦之隔膜,中伤及中焦之胃肠,下损及下焦之肝肾,最终导致耗伤气血,甚则阴阳亡失。形之不存,神何以附。而且它又是一个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变化过程。
一、是正气内虚调适失度。《灵枢?百病始生》指出:“风雨寒热,不得虚,邪不能独伤人。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,盖无虚,故邪不能独伤人。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,两虚相得,乃客其形。”疫邪致病,与自然界中的其它六淫之邪一样,如果人体正气充盛,即使存在导致疫病的邪气,正能胜邪,则正气必将御邪于外,邪气就难以入侵,也就不会导致疫病的发生,正如《素问喇法论》所云: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。不施救疗,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?岐伯日: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。”只有在人体的正气虚弱,不足以抗御外邪时,病邪才能乘虚而入,侵害入体而发生疫病。吴又可继承《内经》的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阐述。他认为“本气充实,邪不能入《经》云:‘邪之所凑,其气必虚’。因本气亏虚,呼吸之间,外邪因而乘之。昔有三人,冒雾早行,空腹者死,饮酒者病。饱食者不病。疫邪所着,又何异耶?”说明疫病的发生,不仅取决于导致疫病的致病因子毒性的强弱,还取决于人体正气盛衰,二者之中,人体的正气是内因,它在预防外邪侵袭,避免疫病发生中,占有主导的地位。
二、是节气违和运行乖戾。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应,认为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,必然受到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的影响,人体的生理变化要与“天地相应,与四时相符”,否则必将导致疾病的发生。《黄帝内经》就宇宙间存在着周期性运变规律,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五运六气学说,旨在探讨自然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及其对疾病的影响。运气“有至而至,有至而不至,有至而太过”(《素问?六微旨大论》)等变化,“至而至者和;至而不至,来气不及也;未至而至,来气有余也。”运气有常有变,节气和合,节至气至,即为天运恒常,则为正气,反之则为异气。即所谓“非其位则邪,当其位则正。”《素问?六节藏象论》云:“未至而至,此谓太过,则薄所不胜,而乘所胜也,命日气淫。……至而不至此谓不及,则所胜妄行,而所生受病,所不胜薄之也”。中医学非常强调人的疾病与气候变化的密切关系,《素问?至真要大论》就指出:“百病之生也,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”,疫病的发生与气候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,不同的疫气具有不同的气候特征,而相同运气的疫气致病,在疾病的证候、转归及预后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。古代中医学家已认识到,天地运气运行乖戾,季节交替违序,导致了自然气候有别于正常时序的更替变化,是瘟疫的发生的原因之一。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,则天地变化之一气也。斯盖造化必然之理,不得无之。”通常情况下,人体机能是遵循正常年份节气交替的规律,适时而动静生长收藏。当天时不正,产生乖戾之气作用于人体时,则使人体气机不能按时伸展,突然郁闭于内,就会导致瘟疫天行。《素问?刺法论》就有“升降不前,气交有变,即成暴郁”的论述。由此可见,中医学认为,节气违和,运行乖戾是疫病发生的原因之一。
三、是戾气侵袭口鼻相染。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疫病的发生是外感了一种疫疠之气,经由口鼻侵犯人体而致。这种疫疠之气与一般的六淫不同,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。明代医家吴又可在他所著的《温疫论》中说:“温疫之为病,非风非寒,非暑非湿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…夫疫者,感天地之戾气也。戾气者,非寒、非暑、非温、非凉,亦非四时交错之气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。”吴又可认为,戾气具是一种肉眼观察不到的微小病物质,“气无形可求,无象可见,况无声,复无臭,何能得睹得闻?”夫物者,气之化也;气者,物之变也。气即是物,物即是气。”戾气导致疫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传染性和流行性。他指出戾气侵犯人体,多自口鼻而入,通过气或接触传染,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指出“此气之来,无论老少强弱,触之者即病,从口鼻而入。…邪之着,有天受(自然空气传播),有传染(患者接触传播),所感虽殊,其病则一。”《诸病源候论》说:“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,则病气转相染易,乃至灭门。”同时,古代医家也观察到,戾气致疫,有大流行和散发的不同。吴又可即指出:“其年疫气盛行,所患者重,最能传染,即童辈皆知其疫。至于微疫,似觉无有,盖毒气所钟有厚薄也。其年疫气衰少,里闯所患者不过几人。”并指出疫戾致病,具有发病急,传变快,病情重,症状相似的特点。戾气异常毒烈,具有强烈的传染性,无论壮弱老幼,触之即得,正如《温疫论》所云:“若其年气来之厉,不论强弱,正气稍衰者,触之即病。…大约病遍于一方,延门合户,众人相同,皆时行之气,即杂气为病也”。
对病位及症状的认识
疫病的病位早在《素问.举痛论》中已有记载:“寒气客于肠胃之间,膜原之下。”及《素问.疟论》曰:“邪气内搏于五脏,横连膜原”。这两篇论述均提到了膜原。其涵义正如唐代王冰所注:“膜谓鬲间之膜;原,谓鬲肓之原”。元代时日本医家丹波元简则认为:“堂膈幕膜之系附著脊第七椎,即是幕原也。”以上所论之膜原,皆指胸膜或膈肌之间的部位。后世吴又可对其涵义又有发挥,如“邪去表不远,陷近于胃……邪在膜原,正当经胃交关之所,故为半表半里”。指明疫疠之邪在半表半里之位。吴氏所论膜原虽与《内经》不完全相同,但二者大体类似,均为非表非里或表里交接之处。
其临床症状表现,早在《内经》中也有记载。《素问.刺法论》曰:“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。”疠气种类繁多,但一种疠气只能引起一种疫病。而每一种疫病不论年龄,不论性别,症状多相类似。因疫疠之邪气毒力颇强,潜伏期较短,常夹火热、湿毒等秽浊之气侵犯人体,比一般邪气致病性更强,甚至触之即病。故都具有发病急骤、来势较猛、病情危重的特点。临床多见患者发热,且热势较高,并伴有烦渴、舌红、苔黄等热象。致病后,极易伤津、动血、扰神、生风,亦易损害心、肾、肝等重要脏腑。若不及时救治,易致病情险恶,甚至死亡。
祖国医学对疫病防治的认识
疫病具有传播迅速、传染性强、传变较快、致死率高、易造成社会恐慌等特点,古代医家和先民为抵御疫情、保护生命、减少损伤,积极应对,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,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。
未病先防,培固正气。对于急性传染病,古代医家十分强调早预防,治未病。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就明确指出:“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,不治已乱治未乱。”如何能有效避免和抵御疫病对人的侵袭传染呢?《素问·刺法论》就有此问:“余闻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,不施救疗,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?”答曰:“不相染者,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”。主张培固自身“正气”,以抵抗“邪气”侵入。吴又可在《温疫论.原病》篇中说:“本气充满,邪不易入,本气适逢亏欠,呼吸之间,外邪因而乘之”。人体正气充盛,杂气不犯;正气亏虚,杂气通过口鼻,乘虚而入,致人发病。明代《景岳全书》《瘟疫·避疫法》也指出:“瘟疫乃天地之邪气,若人身正气内固,则邪不可干,自不相染。”中医认为人的正气主要由精气等物质构成,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说:“故藏于精者,春不病温”,可见对于精的保养十分重要,要藏精就要让精能正常生成,而且不能过多耗散。精的生成是要靠饮食物化生的气血不断来充养,精、气、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,如果气血不足,精就无法充足。气血的生成还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。气血要能充养精,还必须要求气血和顺,情志畅达。另一方面,要防止精的耗散,就不能过劳,包括劳心、劳神、劳身以及房劳,要做到“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”。正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所说:“恬憺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由此可见,培补正气,保持健康强壮的体魄,增强抗病能力,才是预防疫病侵入的根本。
尽早发现,严格隔离。疫病往往萌发悄然,一旦蔓延,气势难挡。因此,及早发现十分重要。《素问·八正神明论》提出“上工救其萌芽”的思想,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头,及时防治,以免疫情扩大,难以遏制。《灵枢·官能》曰:“邪气之中人也,洒淅动形。正邪之中人也微,先见于色,不知于其身,若有若无,若亡若存,有形无形,莫知其情。是故上工之取气,乃求其萌芽。”唐代杨上善释道:“邪气初客,未病之病,名曰萌芽,上工知之。”由此可知,“未病之病”指的是疾病尚未显露症状的阶段。高明的医者能预先发现疫病的苗头,给予警示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也载道:“民疾疫者,设空邸第为置医。”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所治疗,以免疫病传播。
疫病的致病邪气毒力非常强大,正气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,所以避免邪气的侵袭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环节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:“虚邪贼风,避之有时”,《素问·刺法论》强调:要“避其毒气”。要避免疫邪的侵袭,就要讲究个人卫生,对环境消毒,疫病发生后要采取隔离措施,这些在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具体的做法。古人早已知道“病从口入”的道理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·霍乱》中说:“原霍乱之为病也,皆因饮食。”这就明确指出了饮食不洁与传染病的关系。晚清名医余伯陶在《鼠疫抉微·避疫说》中指出,室内通风透光利于防疫:“避之之法,厅堂房室,洒扫光明,厨房沟渠,整理清洁,房内窗户,通风透气。”即使今天,通风透光也是防疫的基本要求。
医疗防治,勇于创新。在与疫病的抗争中,历代医家们勇于钻研和创新,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。东汉末年瘟疫盛行,张仲景发愤写成《伤寒论》,奠定了“辨证施治”的基础;金朝末年汴京大疫,李杲著就《内外伤辨惑论》,创立了“内伤”学说和“甘温除热”思想;明末崇祯年间疫病肆虐,吴又可创著《温疫论》,开温病学说之先河。历代医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方药。如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;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;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、李杲的补中益气汤,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、三消饮、举斑汤,清代吴鞠通的桑菊饮、银翘散,都为疫病防治发挥了显著的效用。
当前,对于突如其来的疫病,我们期待效药的出现。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七版)》指出,各地根据病情、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,参照方案进行辨证论治。祖国医学预防疫戾传染,除远离致病原和刺激经络腧穴的方法,还采用了如吐法、浴法、药法、香薰法及精神调摄法,让心情愉快使正气充盈。重视调养肝气,禁忌大怒。顺应时序,保养正气,吐故纳新。认识到在气血和畅时,人体能充分发挥其防御外邪的作用,身体功能状态失调是感受疫戾之气入侵的重要条件等。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,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,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。在中华民族漫长的繁衍发展进程中,大大小小瘟疫都是以平复而告终,中医药在护佑百姓健康包括防疫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。在今天的抗疫治疗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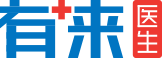
有来医生
祖国医学对疫病的认识及防治初探
2023-02-01
本内容不能代替面诊,如有不适请尽快就医
针灸科医生推荐
